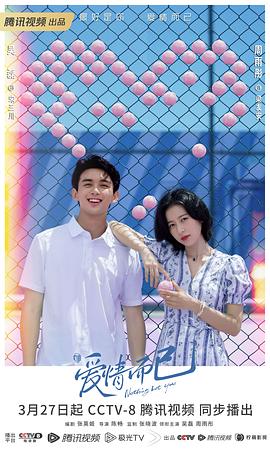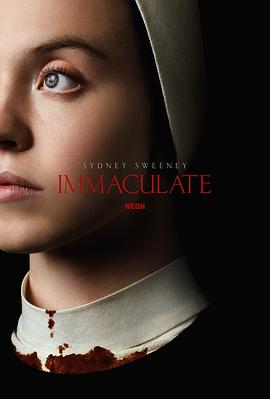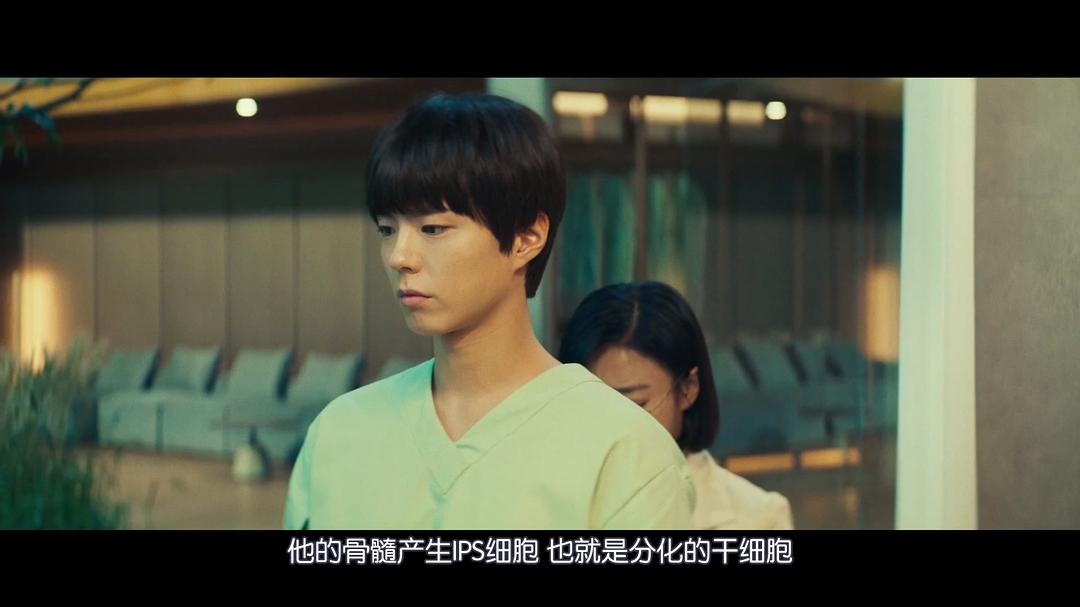曾经辩论如何死去才是最幸福,太多幻想都是电影的桥段,傻傻的流着泪说愿意死在某人怀里,而那个人也信誓旦旦承诺永恒。迷失在那份浪漫的感动里,自以为生命终结可以成就幸福的终极。
在25岁生日这一天看这样的片子,不免有些鬼里鬼气。当年期盼的幸福的臂弯如今停留的不知是谁,再见亦难,样子都变得模糊。死亡没有变的直观,不再那么简单,当你看到眼角居然开始出现细纹。在陌生的城市,独自一人,生命的单程旅行变的越发艰难。
谁能说死别更痛于生离。死亡带走的是肉体,但带不走爱。小孙女会在祖母入殓时记得为她穿上生前希望带走的长袜,妻子会在丈夫额前留下鲜红的唇印,面对死亡,我们满怀欣慰的哭泣,因为爱没有离开。
真正的痛是想爱都难。片中的父亲,离开后满是悔恨至死思念的亲人都不能在身边,而他的妻子坚守那份感情即便一切无可挽回。那颗石头落下时明明猜到这样的桥段还是不由得哭了,只有在最后的时刻我们才知道最值得珍惜的已经不能挽回了。而他又多么幸运有至亲温柔的手来送行,细腻的温柔

故事的始末都给人一些凝重,但也贯穿了若隐若现的活性和生机`.
他扳开父亲的手,一粒乳白色的鹅卵石落下来的那一瞬间,我的眼眶里霎时充盈了泪水...

晚上躺在床上看完这部电影。我想我流泪的原因总归是和别人不大一样的吧。广末凉子拿出小林君父亲的唱盘播放,声音吱吱啦啦的流出来的时候,我竟然哭得浑身颤抖,眼泪就像是从未淌出过一样,疯狂的泻出。一身大汗告诉我,其实我是想念我父亲的。
小时候也曾去海边捡过石头,也如同每个孩子,把捡来的石头宝贝一样的藏在自己的铁盒子里。但却从未听说过片中的故事——这块时候的挑拣也是意味着对亲人的情感。
只经历过一次为往生者送行,还是晚上,却不是我的亲人——是拐了弯的姥姥(中国的辈分总是很奇怪的,什么人都要喊声姥姥)。那时我还小,似乎对生死的概念很模糊。竟也迷迷糊糊的被带进停尸间,看到的是一排被白色被单盖住的死人,只露出微微变了颜色的双脚,打了个寒战。记得脚上挂着写着名字的纸牌。
和大人跪在停尸房门口为死者烧纸,那好像是个秋天,天气微凉,铜盆里的火烤的人倒是舒服。看着扭曲的火焰,一下子就想起姥姥剥蒜、淘米的样子,还会想起她嘴巴里酸酸的味道,浓重的口音,还有她留给我的杨梅。眼泪控制不住流了下来

终于看了入殓师,说终于,是心怀歉意的,对这样一部电影,即使是习于看70年以前电影的我,也不该怠慢如此的。
笹野高史,演那个澡堂子里的老头子。上一次见到他,是在日剧交涉人2里,此人面向甚老,其实是48年的人,入电影行极晚,85年第一次触电是在山田洋次的男人之苦里,在那之前他一直是戏剧演员。据说此人42岁的时候娶了个17岁的老婆。
演社长的山崎努,初看总觉的面熟,后来一查,果然,我非常喜欢的蒲公英里那个长途司机黑郎,就是他。那是20多年前,他还不到50岁,戴着牛仔帽,让我对蒲公英这部戏的印象完全是西部片的感觉。如今看,竟苍老如斯了。我极爱吃河豚鱼白那一段,生死与吃之间的逻辑,了不起。山崎或者笹野这样的演员,中国若能有一两个,就了不得了。
说起蒲公英,其实入殓师让我想起了伊丹十三,他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导演,此人对类型片了如指掌,然而又充满了荒谬感和仪式感,我以为,日本电影的一大特点,乃至日本文化的一大特点,就是把荒谬感和仪式感同时展现,bilateral。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讲bilateral,双边,同时进行,威力无穷。

一个不小心,之前敲下的字瞬间全没了。试了多种方法,无果。
这两张海报都很喜欢。一张现实主义,一张浪漫主义。或者这正是影片中故事的影射吧,既现实又浪漫。
多久没有看影片了。多久没有看影片这样淋漓尽致的哭了。若不是担心影响到别人,我想我会嚎啕大哭。那是一种抑郁在心口极致的悲伤,我多次忍不住要以这样肆意的方式来宣泄。可惜,我只能压抑着声音静静的泪雨磅礴,任凭喉咙干涩胸口生疼。
所以,看极度快乐和极度悲伤的影片都应该只是一个人的事情。
起初,我为影片里太多的死亡而悲伤。
可是,当第二天清晨起床,看到徜徉在屋子里大朵的阳光,豁然明白,原来,那些好吃的让人为难的美食和美妙动听扣人心弦的音乐,还有浓郁粘稠形形色色的爱才是生命的主题。
关于美食。
影片的开始,她在知道他买大提琴花了巨额数目时,不发一言,只说,我去做饭。再怎么样,饭总是要吃的吧。他领了一天的薪水之后买了昂贵的牛肉犒劳她。她开心的像个孩子。这些若有若无的细节,真实而自然的呈现。生活就是这样。或者生命里最容易让人有满足感的就是美食。

“入殓师”匠心!至少,我该记得你的样子的
转载请注明网址: https://www.cjjdcj.com/a/dy-1421.html